作者|趙賽坡
頭圖|視覺中國
本期首先推薦三篇關于伊隆·馬斯克的長文,以周圍人的視角勾勒這位億萬富翁的過去與現在,你會看到控制欲極強、以自己為中心等性格特點,如何塑造他的工作與生活,特別是在收購 Twitter 與探索 AI 風險的過程中,馬斯克的這些性格特點展露無遺,而后兩者,勢必將對人類未來產生巨大影響。
本期還將推薦以下主題的長文:
為什么人類考試不是大模型能力測試的最好方法?
Spotify 的崛起與困境;
“More Reading,Less Junk”,歡迎進入本周的深度閱讀時間。
如果測試大模型的方法是錯誤的,結果會怎樣?
自去年 11 月 ChatGPT 發布以來,我們已經聽到或看到各類模型通過人類考試的報道,特別是 GPT-4 問世之后,大語言模型所展示的“推理”能力或“邏輯”能力,能夠在更多人類考試場景中一騎絕塵。
但就像考試僅僅是人類智力水準的一種測試一樣,即便大語言模型能夠通過這些考試,并不代表其具有人類同等智力。更何況,大語言模型對于應對考試具有天然的優勢,其強大的算力,能夠比人類個體更快、更好獲得考試的結果。
我非常推薦這篇來自《麻省科技評論》的長文(鏈接、30 分鐘閱讀時長),文章向我們展示了當下學術界對于測試大語言模型能力的不同看法,兩個有趣的方向很值得思考:其一,僅僅使用人類考試測試大語言模型是否合適?如果不合適,還有哪些可以考慮的方法?

其二,通過 A 測試的大語言模型無法保障在 B 測試中獲得好成績——即便 B 測試和 A 有相關性,這與人類社會對于智力的認知完全不同,但我們對出現不同測試結果的過程并沒有完整的復盤總結能力。換句話說,當下我們更多在意測試結果,而不是這些模型如何通過測試——當然,逆向一個語言模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和人力成本。
事實上,人類對于大語言模型是否“智能”的判斷,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假設,那就是尋找與人類自身智能相匹配的智能水平。但問題是,我們并不知道大語言模型的“智能”一定與人類相似或一樣,倘若大語言模型是另外一種智能呢?那是不是現在我們所有的對比、測試方向都是錯誤的呢?
圍繞這個話題,再推薦一組延伸閱讀:
人類通常認為語言就是智能的象征,這背后既有歷史文化原因,也暗含了很多人類對自己思維的偏見,Meta(原 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負責人、同時也是圖靈獎得主的 Yann LeCun 救災這篇長文(鏈接、35 分鐘閱讀時長)里詳細探討了這一點,你需要記住,“僅僅依靠語言訓練的模型永遠無法接近人類的智力”。
某種意義上,人類現在對于人工智能的迷戀,也是一種對自身智能的“自戀”行為(鏈接、25 分鐘閱讀時長)。歷史上,人類習慣于在各個場合尋求符合所謂“人類智能”的跡象,從農業社會時代感知大自然不同生物的“智能”到工業革命之后無數個建造機器智能的嘗試,再到 1950 年代以后,計算機、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智能(幻覺)”,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或者說,人類一直在尋找湖中自己的倒影。
收購 Twitter、搶占 AI 話語權,馬斯克要如何塑造人類的未來?
從社交媒體到電動汽車,從烏克蘭戰爭到太空探索,從生物科技到人工智能,伊隆·馬斯克無處不在。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馬斯克現在是全球最有權勢的企業家。
本期推薦三篇關于馬斯克的長文。第一篇來自《紐約客》(文章標題:Elon Musk’s Shadow Rule How the U.S. government came to rely on the tech billionaire—and is now struggling to rein him in.
、50 分鐘閱讀時長),以馬斯克周圍人的視角勾勒這位億萬富翁的過去與現在,你會發現他的性格特點,比如控制欲極強 、以自己為中心等特征出現在生活(婚姻)與工作的方方面面。
更進一步,文章還探討了馬斯克的政治立場,他在很多事情上呈現出極為矛盾的一面:既呼吁市場自由,又不斷強調監管的重要性;既尊重科學,又質疑疫情是一場陰謀;既鼓勵言論自由,又不斷在 Twitter 上掀起一邊倒的聲討運動。
文章里的一個細節,一些馬斯克的同事將他的不穩定行為與自我藥物治療的努力聯系在一起,“他的生活真的很糟糕。太有壓力了。他對這些公司非常投入。他入睡和醒來都在回復電子郵件”,一位馬斯克的同事說道。
第二篇長文來自馬斯克即將出版的傳記,該傳記作者是大名鼎鼎的 Walter Isaacson(曾給喬布斯寫過傳記),WSJ 獲得的這部分內容(鏈接、免費鏡像、50 分鐘閱讀時長)還原了馬斯克收購 Twitter 的全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馬斯克的“賭博”心態,他對 Walter Isaacson 說,“我想我總是想把籌碼推回賭桌上,或者玩下一局”。

整個過程里有幾個重要的節點:首先是特斯拉股價大漲,馬斯克手上擁有了 100 億現金,他不想存入銀行,于是計劃投資 Twiiter;其次,在和 Twitter 管理層的溝通過程中,馬斯克認為這家公司的管理者不夠“狼性”,萌生收購之意。
其三,收購過程發生了很多意外,比如馬斯克一度因為 Twitter 用戶數據造假而想反悔,但律師勸住了這位億萬富翁;其四,馬斯克設計了一套周密的 Twitter 摘牌交易方案,利用時間差制造出來的法律漏洞,不必再向Twitter 原管理層支付高達 2 億美元的賠償金。
第三篇長文也是馬斯克傳記的節選(鏈接、免費鏡像、45 分鐘閱讀時長),話題聚焦于馬斯克過去十年對 AI 風險的探索。
早在 11 年的 2012 年,馬斯克就從 DeepMind 創始人 Demis Hassabis 了解到 AI 的潛在風險,他有了通過投資以進一步認識并控制這些風險的想法。馬斯克將 Demis Hassabis 介紹給 Google 聯合創始人 Lary Page,后者盡管不認同馬斯克關于 AI 風險的觀點,但對 Demis Hassabis 以及 DeepMind 的技術非常感興趣,并在 2014 年搶先買下了這家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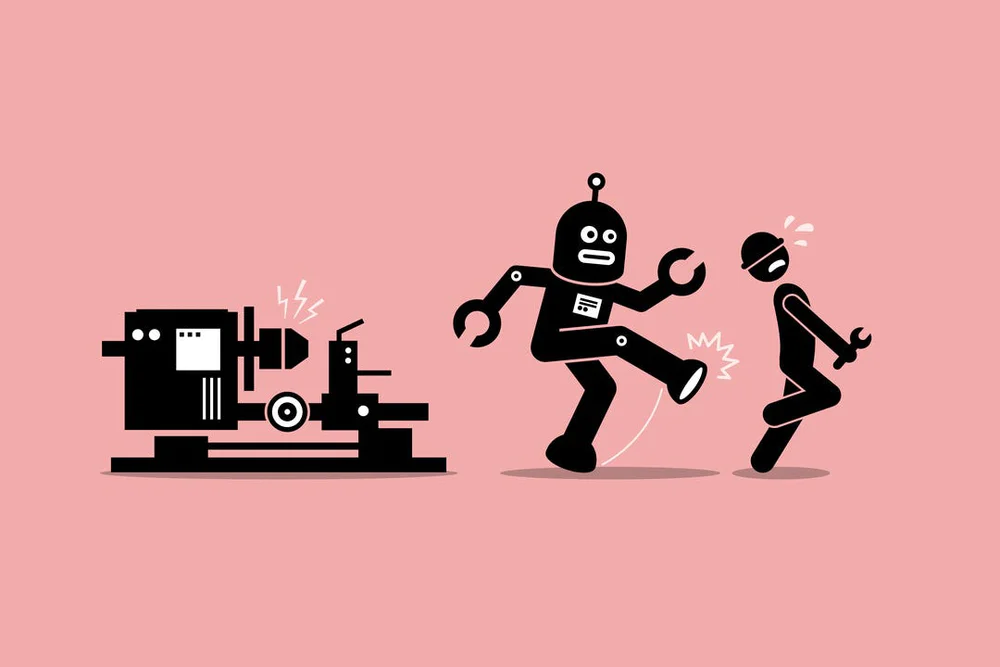
失去 DeepMind 對于馬斯克的打擊很大,在他看來,AI 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技術,不能由一家或幾家大公司控制。馬斯克于是尋找新的路徑,他與 Sam Altman 的幾次會面,敲定了一家非盈利、面向產業開放的新 AI 公司——OpenAI;與此同時,馬斯克還希望通過建立更緊密的人機關系以杜絕可能的災難,這成為腦機接口公司 Neuralink 成立的背景。
但在 2018 年,馬斯克因為無法說服或者說控制 OpenAI 加入特斯拉而放棄了這家公司。后面的故事已經走到了另一個方向:OpenAI 與微軟結盟,并推出 ChatGPT,震驚世界;馬斯克買下 Twitter,屏蔽了眾多 AI 公司的數據訪問權利;馬斯克成立了自己的 AI 公司,利用特斯拉汽車、Twitter 上的海量數據訓練新的 AI 模型,他開始做一件他最擔心也最討厭的事情——將強大的 AI 控制在某一個公司或某一個人(伊隆·馬斯克)手里。
Spotify 的崛起與困境
Spotify 是目前音樂流媒體無可爭議的霸主,了解它的發展歷史,基本就能知曉過去近二十年互聯網音樂的演化歷程。這篇來自 LRB(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長文(鏈接、50 分鐘閱讀時長)借助兩本關于 Spotify 的圖書,勾勒出這家流媒體巨頭崛起、迭代的關鍵事件,包括:
這家公司的出發點是要杜絕音樂盜版,彼時全球音樂盜版最瘋狂的地區就是瑞典,Spotify 就誕生在那里;
Spotify 與音樂行業的分成模式是通過播放次數進行付費,但在 2/8 定律之下,頂級藝術家仍然可以賺取數百萬,但較小的藝術家幾乎沒有收入;
Spotify 改變了音樂應用的產品邏輯,個性化推薦、自動播放等技術或功能已經成為流媒體音樂產品的標配;
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Spotify 還沒有盈利,但它在音頻行業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或者說,Spotify 的影響力遠超于商業能力;

我還選了一篇本周 WSJ 的頭版文章(鏈接、15 分鐘閱讀時長),通過公開數據和調查采訪,復盤Spotify 投資 10 億美元構建播客產品的失敗過程。
Spotify 播客戰略的核心是通過與一系列名人或工作室的合作,創建一些獨家節目,以此吸引更多聽眾使用或更頻繁使用 Spotify,在持續增加聽眾——無論是免費還是付費聽眾——的同時,賣出更多的廣告。
但現實格外殘酷,一方面,獨家播客節目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但另一方面,播客市場的廣告商卻格外吝嗇,Spotify 在這樣的雙面夾擊之下不得不縮減播客團隊,并試圖與一些名人播客共享收入權益。


評論
最新評論